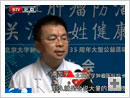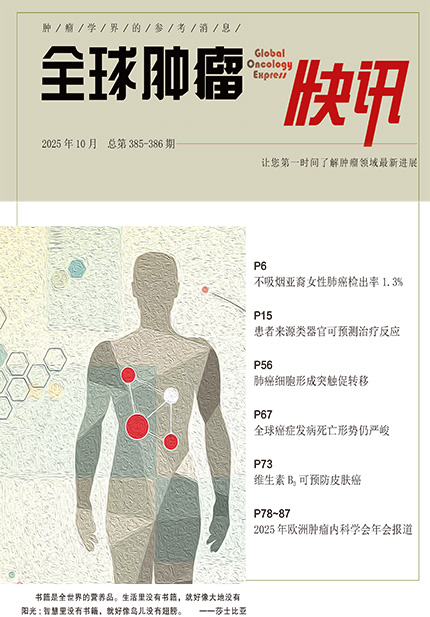梅奥诊所印象
---梅奥诊所印象
2013年3月-9月我获得院攀登计划的资助赴美国梅奥诊所(Mayo Clinic)做的访问学者。
当我在Siebens五楼前台旁的沙发上坐下时,我知道我的Mayo之行就此正式开始了,心中一通莫名的兴奋和紧张。尽管前台的秘书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各自周末的趣事,我却陷入了对这个陌生地方的无限憧憬中。窗外静静地飘起了鹅毛大雪,取代了昨天纷纷的小雨。这里的人不会也像天气般诡异吧?很少跟老外打交道的我不禁有些忐忑。很快我就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”了,从电梯间又转出一个清瘦的东方女性,让仅来了2天的我突然觉得很亲切。难道是微信里的朋友?但当她操着纯正的日式英语和秘书问候时,我承认我想多了。没多久Reilly(分管访问学者项目的高级秘书)就从工作区的窄门闪了出来,用她缓慢且清晰的英语给我们做简短的Orientation。此时,又来了一个年轻小伙,好像是这里的老板专门派来引领这位日本内科大夫的。他随即成为了我们的临时导游。他一边带着我们在大楼内部穿梭,一边声色并茂地讲解着,热情且自豪,倒有点像是给好朋友介绍自己的家。
“Mayo诊所是Mayo兄弟在19世纪末共同建立的,一开始就在Rochester,1987年又在Arizona和Florida成立了分院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大型的非营利医疗机构。拥有床位2500张,员工5万多名,其中大夫8000人。年门诊量60多万,住院13万人次……”他如数家珍般地介绍着,我却在怀疑这么多的数字作为一个普通员工的他是如何记住的。出了电梯,他没有直接领我们走出Siebens Building,而是拐到了与之相通的另外一个大楼Plummer Building。刹那间满眼的富丽堂皇,和现代简约的Siebens相比,简直让我以为穿越了。这里据说是Mayo最早的医院大楼,至今快100年了。当初是按照高级酒店的标准建造的,现在已经作为Mayo高层的办公楼。从它满是镶嵌和雕刻的大门出来抬头仰望,顶层金灿灿的钟楼让人觉得它更像是一座神圣的教堂,里面的人在奉耶稣基督的名,济世救人,无私地帮你解除痛苦,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,也许这就是大楼的设计者要表达的初衷和希冀,然而时至今日,又有多少医院和医生还能秉承这种理念和宗旨呢?“那就是Mayo Clinic”。我不由地顺着“导游”的手指看去。一座近20层的现代大楼横在我们面前。说它“横”是因为它有2个街区长。于是,古典和现代就这样相望着矗立在小巧的Annenberg广场两侧。而广场上最出名的就是Mayo兄弟的铜像了。说实在的,一开始我真没看出来。因为它们并没有被安放在什么大理石基座上,而是很随意地坐在了诊所门前的台阶上。我不禁想起了Harvard校园里最出名的铜像。传说摸了它就能考上Harvard,可是铜像架在了1人多高的石基上,于是整个铜像只有大家能够到的鞋子被摸得锃亮。而这对兄弟若干年后被摸得最亮的地方也许会是肩膀吧,因为他们的姿势很容易让大家搂着。
置身于Mayo Building以及和其贯通的Gonda Building的华丽大厅中,厚重的大理石装饰让人油然有种踏实的感觉。再透过玻璃窗看看外面漫天的飞雪,从3层挑高屋顶洒下的暖暖灯光,又让人豁然有种超脱的感觉。这就是Mayo,美国人最看好的医院(据说15%的美国人生病后会考虑到Mayo看病)给人的第一印象吗?她还有什么神秘的过人之处?一缕琴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在一个明亮的角落里摆放着一个崭新的三角钢琴,一位白发的老者正坐在那里悠扬地演奏着,不时还扭过头去对着坐在轮椅里的同样白发的老伴微笑。老伴也和着琴声点着头,打着拍子。一曲奏完,旁边几位驻足的聆听者轻轻地鼓掌表示鼓励。老者随即又微笑着推着老伴消失在大厅的人群中。我这时才开始注意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人们。那些步伐较快但很稳健的一定是工作人员吧。可是其他的人怎么不像看病的啊?我看不到患者脸上痛苦挣扎的表情,看不到家属着急惊慌的目光,看到的是一副副安逸平和的笑容。似乎他们确定已经到了他们该到的地方,剩下的就全交给医院了,这里会给他们最好的治疗。这就是Mayo的口号之一Destination Medicine(目的地医疗)的魔力吧。这般生死相托的信任难道不是对Mayo“患者至上”服务宗旨的最好回报?
“这是Heritage Museum(遗产博物馆),我对Mayo的历史知识很多都是从那里获得的。Hi,Patricia”他一边介绍着,一边跟唯一的管理员打着招呼。展厅应该不大,门也很不显眼,望过去都是一些历史照片和捐助的物品。由于着急赶路,我们并没有进去。幸好一路上他仍旧可以不停地给我们介绍。“这里面可都是各国捐助的好东西啊,其实整栋Gonda Building也是一个犹太人捐的,他捐了10亿,可惜大楼没盖完就死了,他儿子又捐了4亿才完工。和其他医院不同,捐助收入占Mayo收入的很大一部分。从Mayo兄弟在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不过,现在已经没有姓Mayo的在董事会了,他们家族4代出了7个大夫……”。他不停地介绍着,即便是爬楼时气喘吁吁的,也没有停止。但是当他走到一个房间门口时却停下了。“你们猜猜这是做什么用的?”说它是个房间,可是没有门,里面是个圆弧形影壁,周围的墙上龛有一些雕塑并打上了柔和的灯光。绕过影壁是个15平米左右的房间,没有任何的家具,房顶局部做成了圆形也打上了五彩的灯光,和同样拼成圆形的地面瓷砖对应,再加上半圆的影壁,形成了一个圆柱形空间。他并没有让我们猜得太辛苦,直接告诉了我们答案。这是个让人缓解情绪的空间。我恍然大悟,难怪雕塑中又有基督,又有圣母,还有佛爷的。快从影壁转出来的时候,我看到壁龛内有一本书,封面写有阿拉伯文字,周围也装饰成伊斯兰风格,估计是《古兰经》。由于伊斯兰教有向圣地麦加朝拜的习俗,经书摆放的方向可能就指向东方的麦加。我为了挽回刚才没有猜出来的颜面故意指着那本书问道“那边是东吗?”他很诧异地看着我“是啊,我还以为你会转向”。“因为Mecca(麦加)在那个方向”我有些炫耀的说。“Here is Mecca,Medical Mecca”他微笑着说,但语气丝毫不像是开玩笑。这次轮到我诧异了。他真的很自信,并且为自己的医院自豪。
接着我们到了照相室,10分钟后我就拿到了我的胸卡。他告诉我如何到外科门诊,在那里可以找到Kendrick(我在Mayo的导师)的秘书。我匆匆告别了这个热情且自信的小伙子,来到了12层的外科门诊。前台有2个秘书,而对面整齐码放的沙发上已经安静地坐了20多人。前面没有人排队,我径直走过去说明了我的来意。其中一个秘书让我在旁边等候,她进到后面的办公区去找人。其间我看到很多带胸牌的人进进出出,还穿着西服。后来才知道这里出门诊和查房是要穿西服而不是穿白大衣的。实际上,Mayo也始终没有发给我一件白大衣,我也觉得确实并不需要。因为去手术室会有另外一套衣服,而平时基本就是西装,以示对患者的尊重。Kendrick的这个秘书是个干练的50来岁女士,负责临床以外的一些事物。她对我很热情很亲切,因为我们之前书信来往已经半年多了。她说kendrick已经上手术了,所以派个人直接把我送去手术室。送我的人也是一个40多岁的女士。她说kendrick的病人都是在Saint.Marys医院做手术。我们要坐Shuttle Bus去。原来Rochester 的Mayo分为三个院区,Saint. Marys,Methodist和Mayo Clinic。后2者挨得很近。去St. Marys步行则需要20多分钟,所以一般都坐这种5到10分钟一趟的摆渡车。当然,摆渡车还有其他的线路,如到宿舍的,到其他中心的等等,都用颜色区分开。为了把近处的停车场留给患者,Mayo员工的车都停在了较远的停车场,通常也是坐这种免费的摆渡车来医院。
在路上她介绍说St.Marys医院是1888年修道院建的,后来修女们把它卖给了Mayo,据说是只卖了1美金,但要求Mayo兄弟要以慈善为目的,以患者为中心地经营医院。看来Mayo兄弟实现了他们的诺言,他们筹建的基金会也一直秉承着这个宗旨。
我们在这个“回”字型的St. Marys医院里前行。大楼的四个角是各是一个building,算一个病区,但是病房都是开放的,没有病房门。我很快就迷失了。她可能注意到了,顺手从墙上分类放置的小册子中拿了一本地图给我。我却盯上了其他的手册。种类很多,有围手术期注意事项,有康复指导,有心理辅导,甚至还有戒烟指导。而每个病区根据病种不同也有不同侧重。相同的是,每个手册封面上都有一行小字,“patient education”。墙上还有其他的展板,有奖状,有医师照片,有感谢信,有哪个患者最近过生日,患者自己填写的喜好,以及和患者的合影。布置得很细致、温馨,就像真的把这里当成了家。
我换好衣服出现在手术室已经9点了,但我真的没有想过来Mayo的第一天就顺利地到了手术室,跟kendrick见的第一面也是在手术室。他跟我仅简单地寒暄了几句,就又开始专注地手术了。做的正是他的拿手好戏,全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。他至今仍保持着这个手术全美例数最多。台上除了他还有一个扶镜子的Surgical Assistant和一个剪线需要10秒钟的住院医。但他似乎并不着急,让住院医主刀切胆囊。漫长的40分钟过去了,他却依旧耐心地鼓励着住院医直到胆囊完全从肝脏上切除。我估计对他来说,最多用10分钟的步骤却因为训练这个生疏的低年资医师白白损失了半个小时。但当我看到住院医眼神里流露出的满足和自信时,我觉得这半个小时确实值得。Kendrick的动作熟练流畅很多,手术顺利地在12点就结束了。然而旁边的屋子里,另外一个同样的手术在等着他。他顾不上和我多聊几句,就刷手上了台。刚才那台的住院医忙完了也跑过来一旁观摩。可不一会他却在一旁的电脑上玩起了“游戏”。这实际上是一个模拟切除胆囊的课件,是这里的一个主治医师制作的。课件先讲解,然后需要“玩家”按照要求进行操作才能进行下一步,并最终完成整个手术。这次,这个住院医很快就“通关”了。他说,他以后要多去Simulation Center(模拟训练中心)去进行更真实的腔镜模拟训练。而这个中心是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。这时,推门进来一个老教授。“Farnell教授是原来的外科主任,快退休了”好心的住院医小声地在我耳边介绍着。Kendrick主动跟他打招呼,问他的腹腔镜胰体尾切除做得如何。Farnell坦诚地说,刚开始做还不太熟练。我很惊讶,一个快退休的老主任会去主动学习腹腔镜,而且还在若干低年资医师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。也许正是这样的胸襟成就了这么卓越的团队。
手术并不算太顺利。因为肿瘤侵犯,需要切除部分肠系膜上静脉。Kendrick在腔镜下完成了血管的切除吻合。等手术结束时,也已经6点了。我以为Kendrick终于有时间能和我说几句了。可他只跟我说了他的手术安排。还有明天早上有个肝胆讨论会,6点半,我若感兴趣可以参加。他还要去见家属,告诉他们手术延长的原因。然后就又匆匆地走了。我来Mayo的第一天也就这么地结束了。然而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时差,我却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。
出来时雪已经一尺厚了,分不出是便道还是一旁的草地。我向着家的方向摸索着,同时也在思考着。Mayo值得我们学习的绝不仅仅是临床技术。百年的Mayo是如何在患者中建立良好的口碑,又如何在医疗体制变化如潮的今天一步一个脚印,稳步向前的?是始终如一的“keep the need of patient foremost”(患者需求至上)的崇高信条,是平等互爱、团结协作的无私精神,是奋发进取、舍我其谁的主人翁责任感推动着它坚定而又持续地向前迈进。正如Leonard L. Berry在《Management Lessons from Mayo Clinic》一书中阐述的,它是“战略与价值观相融合,创新与传统相结合,智慧与协作相搭配,科学与艺术相统一”的体现。我脑海中又浮现出演奏老者和老伴的微笑;浮现出资深的医者对那个年轻住院医的微笑;浮现出“导游”和那些默默给予医生支持的工作人员的微笑。他们的笑脸化作为三枚捍卫生命的盾牌,组合成了深刻人们心中的Mayo标志。

Plummer大楼的门,这是梅奥诊所最早的住院楼的大门,现已作为高层管理者行政办公用

门诊大楼台阶上的mayo兄弟塑像

梅奥诊所历史博物馆

钱红纲医生同梅奥诊所普外科主任合影